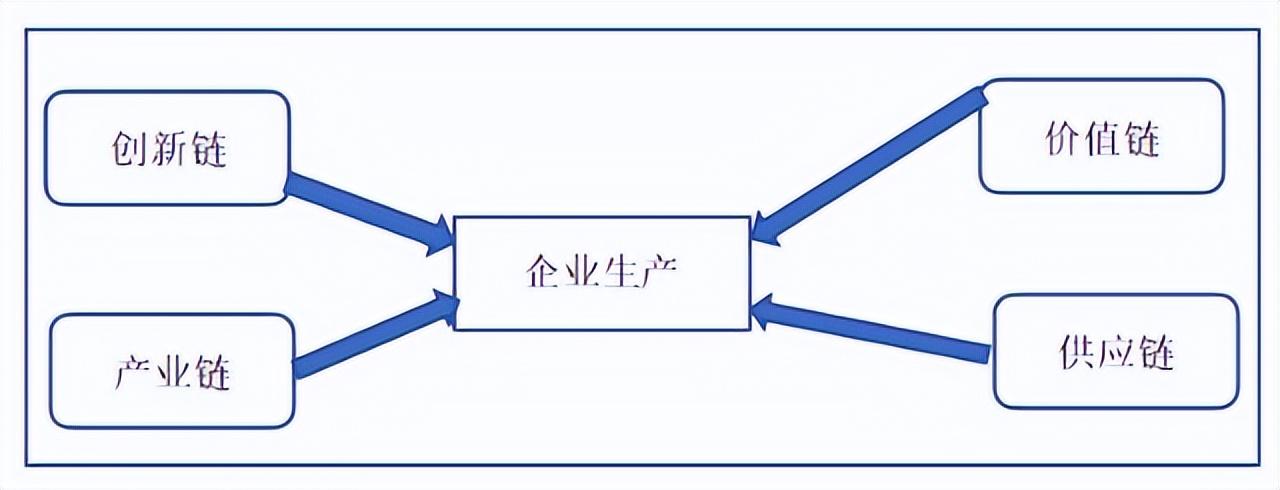图 /文:谢娜利

我有点色,喜欢看美女,尤其爱看爱笑的美女。
可,面对她的笑,我却有些忐忑。这不安从见她第一眼起,便沁进了胸膛,且越沁越深……
春去夏来,万物生灵勃发。我与她相遇在一堵围墙下。此时的天空,像一块即将垮塌的铅块,风雨欲临。我的眼帘,被挂在围墙的铁丝网上。那银灰色的箣篱,骑在白灰色的墙头,朝着深灰色的天空,迸射出一种耀武扬威的灰寂与悲凉。

她立在这片灰朦中朝我灿灿地笑。圆圆的脸,一件黑底白碎花连衣裙,将她覆盖得谦躬而微弱。我莫名地望着她,莫名地看着她的笑容。
围墙中间嵌着一张厚重的大铁门,铿锵凝重威猛。她掏出钥匙,熟练地开启铁门上的小门页。门内,顿时一片喧哗,宛若多国音际组成的和声。我无法识得半词。门开半尺,她将身子坎在门中,右手撑门框,左手握门页,回头朝我笑:快,快进去。一只轮椅的扶手已堵在了门边。
我犹疑着挪步,没等身子完全进入,铁门便“咣当”关闭。一群形态夸张的男女,张着笑脸,涌在门边。喧闹声俨然成了有节拍的单音合奏:“丹丹”,“丹丹”,抑或“妈妈”,“妈妈”。那个拥在最前面的轮椅上的男子,一手握着轮椅把手,一手举着一张白纸,英俊的脸庞仰向她,嘴里念念有词。他椅子上的屁股下,是两只空空的裤管……我尽管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,但此刻还是没能忍住泪水喷洒。
围墙里有个不小的院子,院子中的色调很和谐。油绿的树,葱郁着四栋白色的房子,白色的房子夹裹着一个不小的广场。广场上,黄色的泥土被灰白的水泥通道规划;泥土里嫩绿的菜苗在抽着新芽,通道上有踉跄着、掺扶着,或坐、或走、或站,穿着蓝色背心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;大型的红色舞台,在广场东头,有一股朝阳的气势;“心手相牵,让爱飞翔”八个白色的字,犹如八列在朝晖里欲振翅而腾的雁。

这里,便是湖南有名的“宁乡市欣云愽爱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”。那个一脸笑容的女子,便是创始人欧丹。因她不愿称这群特殊的人为残疾,她和她的同事一致将中心以“学校”敬之,从而,寄养在这的上至65,下至16岁的近80名智障和肢体残疾者,都恭为学员。
虽名为“学校”,其功能却远比学校复杂得多。这里有照管学员日常生活的一切设施和护工,像照顾婴儿般,为学员的穿衣吃饭、屙屎撒尿操心。这里还有从精神上引导,让学员们克服困难,学知识,长见识,领悟做人的尊严和快乐的老师和教程。如:培智班,用以帮助智力障碍严重的学员,学说话,学认字;辅助性就业班,用以教一些弱智力的学员,学会力所能及的劳动,让其获得劳动报酬,促其增加自食其力的信心;电脑班:用以帮助重度肢体残缺的学员,重拾生活勇气,用他们健全的智商,一定的文化基础,学习电脑操作,从而学得更多的知识,做电商,写文章。
我含着一眼眶泪,围学校走了一圈,观看了学员们敞亮的教室、宽大的手工室、精致的工艺品陈列室、直播间、健全的保健室、整洁的寝室、干净的餐厅、飘着檀香的厕所……
我还有幸观看了学员的演出。舞台上,学员拼尽全力,让自己歪斜的身子坐正,站稳。他们使劲地伸着自己伸不直的手,表演手语舞;他们使劲地扯着自己敞不开的喉咙,表演大合唱;他们使劲地读着吐不清的词汇,表演诗朗诵。

台上的学员努力而认真地笑着表演,台下的学员兴奋而真诚地笑着鼓掌。可我怎么也笑不出来。我狠狠地用自己的左掌心,抽打右掌心,那刺痛的啪啪声,是我此刻唯一的表达。这是一场无法从艺术角度衡量的演出,但,它绝对是一场震撼灵魂的演出。那一张张笑脸下,舞动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渴盼,唱出的是对命运之神的诉求。
谁会想到,那个坐着轮椅,排在最前面,嗓音最响的男子,曾九死一生,把生命当累赘。他曾经是个伟岸而帅气的大丈夫,几年前刚结婚便去南方打工挣钱养家。可,没半年,在一次事故中被机器轧去了双腿。他,成了废人。他怕连累新婚妻子,便强迫她离婚。妻子走后,他跟老父住在深山中。
老父既要种田种菜养活他,还要接屎接尿护理他。面对父亲一天天变白的头发,面对父亲一天天消瘦的脸庞,面对父亲一天天弯下的脊骨,他一次又一次自杀,却一次又一次被救活。他不想活,不想拖累老父。在生无希望死亦无门的状况下,他不再开口说话。他用沉默,对抗残酷的现实,他用沉默,折磨着自己青春的生命。几年后,他丧失了语言能力,再也无法吐出一个清楚的字音。

一年前,欧丹听到他的事后,便爬过几个山头去寻访他。当她看到他躺在破烂的被单上,如人彘一般等死时,这位天天泡在残缺中的人,脸上的笑容也被冻僵。她苦口婆心,用党的政策和学校的图片说服他,将他劝到学校。经过一年精心的调理帮助,他整个人都变了,不仅会讲一些简短的句子,而且会写文章,编公众号,做直播。用他自己的话说:活过来了。
整整一天,欧丹用她盈盈笑脸一直陪着我们。我,自始至终没能抽扯出半丝笑意。晚上,我辗转无眠。那种锥心的疼痛和难言的悯惜,把我的情绪搅得如海啸般汹涌。我,忍无可忍,拔通了她的电话。
电话那头马上有了反应:谢姐好!还没睡啊。抱歉,这么晚打扰。没事,我刚加完班,在回家的路上。我仿若看到黯寂的乡村公路上,那张笑脸在飞。我心倏忽忿忿:你为什么笑得出啊,我实在无法理解你的笑,我不相信你的笑真是由衷的。我不信!我的语气充满了疑惑且咄咄逼人。车轮“嗖”地一下,停在我的话尾。然后,一片死寂。
我以为戳到了她的痛点,我以为她无言以对。我不依不饶:请你告诉我,怎么能够在那样一群人中笑得那么坦然。
静默,静默,电话像置于幽冥的黑洞中。我忽感不安:你没事吧?车没事吧?请给我回个音。我话音未落,“哇——”手机里一声嚎啕,吓得我魂飞。没,没事……“嗷嗷”“嗷嗷”声声恸哭,砸碎了凌晨两点的寂寥。

那张灿烂的笑脸,此刻在黑魆魆的乡道上,在孤寂寂的方向盘上,扭曲成叠满故事的旧书籍。或许,从中心创立至今,四年走过的历程,只有这条黑漆漆的乡村公路知道。或许,欧丹笑脸后面的艰难,只有这个能容她头颅歇息的方向盘知晓……
欧丹是学医的,有份好工作。四年前,她因帮忙照看自闭症侄女,而萌发助残之心。在残疾好友的鼓舞下,毅然辞职,与其一起创办了“宁乡市欣云博爱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”。
开始时,四个创办人同心同德,愿将“助残”事业当终身奋斗目标。然,做事业可不是做事情那么简单,“助残”更与“助人”有天壤之别。创办的艰苦,一点一点磨耗掉他们美好的初衷……
中心是免费托养,虽有政府资助补贴,但刚开始筹建时一切都得靠自己。一年下来,四位创建人,添进去的是自己多年辛辛苦苦挣回的钱,得到的是家人的不认同,亲友的不理解,社会的不承认。在没有进款却需无限付出时,矛盾便接蹱而来。在努力付出却得不到认同时,矛盾便加级加深。他们会因学员爬出围墙,四处寻找而相互埋怨。会因学员打架闯祸,而相互指责。会因没钱发护理的工资,而相互责难。诸多的矛盾纠结升温,终于在一年后爆发。他们累了,他们烦了,他们不想干了。
谁来接手啊?没人接这个费力不讨好的烫手山芋。学员们怎么办啊?让他们回家去过以前那种没尊严,无人格的日子?欧丹连续几天没合眼。她心里塞满学员。她想起了“国国”——一个从小就熟识的“怪人”。

欧丹记事起就害怕“国国”,不止她,村里所有的小孩都怕。那时候谁家的孩子不听话,父母定然会拿“国国”来吓唬。“国国”嘴歪眼睛斜,口水满脸,头上长草,走路一边倒。他模样怪,见到孩子还“哇,哇”乱叫。那怪模样怪声音,吓得孩子们哭,吓得孩子们躲。欧丹也一样。连村上的大人们见了“国国”也一脸嫌弃,有的朝他吼:滚开些。有的朝他吐痰:背时鬼。
中心成立后,欧丹第一个把“国国”接来了。此时的她,不再是年幼的孩童,此时的她不再是无知的村姑。她的学识,她的怜悯之心,都鞭挞她曾经的“歧视”。她要“赎罪”,要用自己的爱来温暖这个与父亲同龄的叔叔。可是,现在又要放弃他吗?要放弃这个几十年才体味到人间温暖的“国国”吗?
欧丹还想起了几个从路边“捡”来的学员。她回忆起第一眼见到他们的情景:有的头被打破了,有的不记得回家的路,有的睡倒在大路边。她还想起他们进中心后的笑脸,想起他们一天天趋近正常的生活。现在,怎么忍心又一次抛弃,刚刚树立了一点点自信,刚刚有了一点生命希冀的他们。她实在不忍再看到他们又回到过去,过那种没有希望、没有信心、没有人格的日子。
经过灵魂的鞭笞,她决定:不改初心,独自接盘,独自承担这份万斤重担。

没钱,她借遍了所有的亲戚、朋友、乡邻,几千、几万、几十万。四年来她投入了140多万元血汗钱。没人,她找来了老父亲、小叔子、婆婆。她把父亲的一头青丝熬成了白发,把婆婆对自己那份浓浓的爱,分给了学员,把小叔子当成学员安全的保障。更有意思的是,她将一对学员的母亲请来学校当护工。她要让学员家长那份特殊的爱,感动所有的学员,感染所有的老师和护工。
曾经的合伙人视她为怪物,与她断交;丈夫以离婚要挟,迫她放弃。她没动摇,她用坚定的脚步,坚毅的意志,决绝地走在艰难的“助残”路上……
我在手机里听她哭了一个钟头。我任凭自己的泪和着她的泣涕横流。尽管我担心夜太深不安全,却不忍打断——她该发泄啊,她要发泄啊,不然,那颗拳头大的心脏,怎能承受泰山般的责任和压力。
她抽搐着对我喊:我不能在人前哭啊,因为我不想贩卖悲伤以求怜悯。我更不能在学员面前哭啊,因为我的泪会侵蚀他们羸弱的心,会伤害他们脆弱的自信。我的笑是真的啊,看到有的学员智力一天天提升,看到有的学员能做手工挣钱,看到有的学员嫁人生子,我是真心快乐啊!何况现在国家政策越来越好,何况现在爱心人士越来越多。我真的感到越来越快乐。

我沉默。我无言以答。挂断电话后,东方已见鱼肚白,窗外的树,对着我舒适的家,摇出墨绿的影。从中心买回的一堆学员的手制工艺品,在影中闪出晶亮的光。我找出一个男孩送我的钥匙挂,仿佛看到男孩歪斜而纯真的脸——真惭愧啊!一个残障孩子,因为买了他的手工艺品而知感恩。
作者简介
谢娜利,湖南长沙市作协会员,宁乡市诗散文协会理事。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发表于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杂志和网络平台。出版长篇小说《湘水烟云》。
 关注
关注
 环球电视网
环球电视网

 2022-05-26 09:31
2022-05-26 09:31